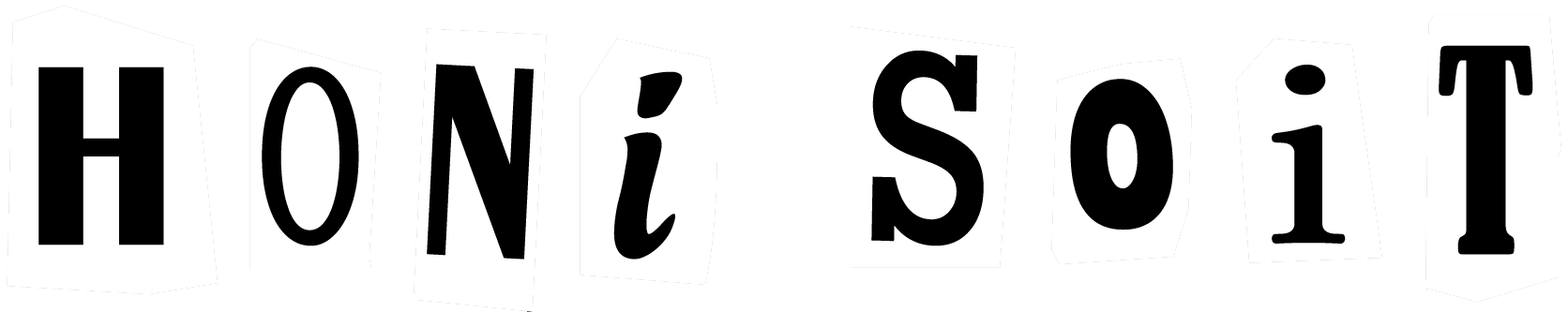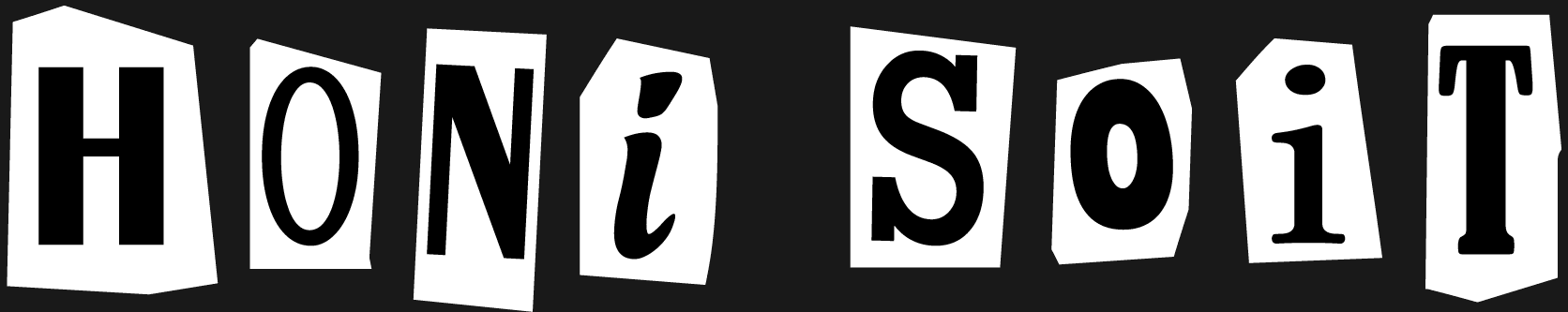今年一月,中国爆发新冠疫情,我决定提前回澳洲。通过两次机票改签,我买到了一月底从上海飞往悉尼的机票。我的父母开车三小时把我送到上海的机场。因为在上海住旅馆会增加感染的风险,他们又要连夜再开三小时的车回家。妈妈在离开之前哭了:“你每年只有暑假回来几个星期,现在居然又提早过去!”,但她也知道这是更稳妥的选择。我成功来到了悉尼,准备完成我最后一年的大学学业。
降落在悉尼机场之后,两名检疫人员上机检查。他们穿着全套防护服,但没有为我们测体温或者进行其他的检查,只是询问乘客和机组人员有没有人不舒服,然后给每个人发了一张COVID-19防治海报。随后我们进入机场,和平时一样,我刷电子护照自助入关,在行李转盘处提了我的行李箱。我并没有带需要向海关申报的东西,所以进入了无申报通道,径直出了机场。在中国被肃穆,悲伤和严阵以待淹没的我仿佛进入了时空隧道。冠状病毒似乎在这个世界里并不存在,我又回到了几个月前我离开时的澳洲,这里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,除了飞机上发海报的检疫员。
但是,在我到达的一天之后,澳洲政府突然发布了对中国的“禁飞令”。滞留国内的中国留学生们,只能选择在国内交同样的学费远程上课,或者花费更多的时间,金钱和承受路途上的感染风险从泰国等地中转,再或者准备休学,等待禁飞令的结束,而谁也不知道会等多久。在电话中,妈妈对我说:“还好你已经到了,我们选的时间真是太对了!”微信朋友圈里,还在中国的朋友们写着各种愤怒,伤心,求助求建议的话。
经过两周的自主隔离,我迫不及待地走上街头,准备去我最喜欢的寿司店。三个孩子骑着儿童自行车从我身边过去,一个孩子突然停下来,指着我说:“哇,快看她,她是病毒!她是病毒!”已经骑远的两个孩子发出夸张的,惊恐的叫声,随后三人一道骑走了。整个过程中我难以动弹,甚至话也说不出来一句。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是我家附近学校的制服,这些孩子最大也不会超过十二三岁。在我住在这个街区的三年里,我们曾经有多少次的擦肩而过?而现在的我在他们面前连一个人也不是,只是一个遥远的国家送来的,病毒的具象化。而在朋友圈里,我的三个朋友已经结伴到了泰国,入住了曼谷的酒店,等待着十几天后踏上澳洲的土地。
来到澳洲的几年间,我越来越觉得,这里的“中国人”是一个抽象化的整体:有了疫情,我们要禁飞“中国人”,这样我们就会万无一失。因为病毒是中国的。而个体的中国人则不在关心的范围之内:如果你在禁飞前进入澳洲,那么没关系,这个中国人不是威胁的一部分。如果只差一天,没办法,这个中国人就来不了。这种抵制或欢迎抽象化的中国人的话术我已经听了太多遍:我们应该让中国人到澳洲旅游买东西,上学,因为他们很有钱。中国人即使移民了也不是澳洲人,因为他们语言文化不一样,这是对澳洲的入侵。“中国人”是一个遥远的符号,所象征的东西从上世纪的陌生的口音,“落后”的文化,变成了穿戴奢侈品的移动金库,再到现在的中国的病毒,但却从来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我们是被打包送上澳洲“文化多样性”(multiculturalism)货架上的巨大而面目模糊的商品,唯一的商标是我们的“原产地”。我们向周围望去,周围其他“商品”的包装上有“传统文化”,“历史溯源”,“考古发现”,而人却是失声的。新冠疫情中,这种话术失效了,因为病毒攻击的正是个体的人,病毒不区分这是被他者化的中国人 / 亚裔,还是其他的种族,国籍。讽刺的是,只有这种漠视让整个社会付出巨大代价之后,一部分人才能惊醒:原来我们都是人,我们都活在此刻,活在这里。这也许映射了更深的攻击:在没有病毒的世界,被这套话术操弄和攻击的并不是抽象化的“中国人”,“有色人种”,“少数族裔”的概念 —— 一个概念永远不会受伤。被伤害的我们,这些活生生的人,则是难以动弹,静默无声。